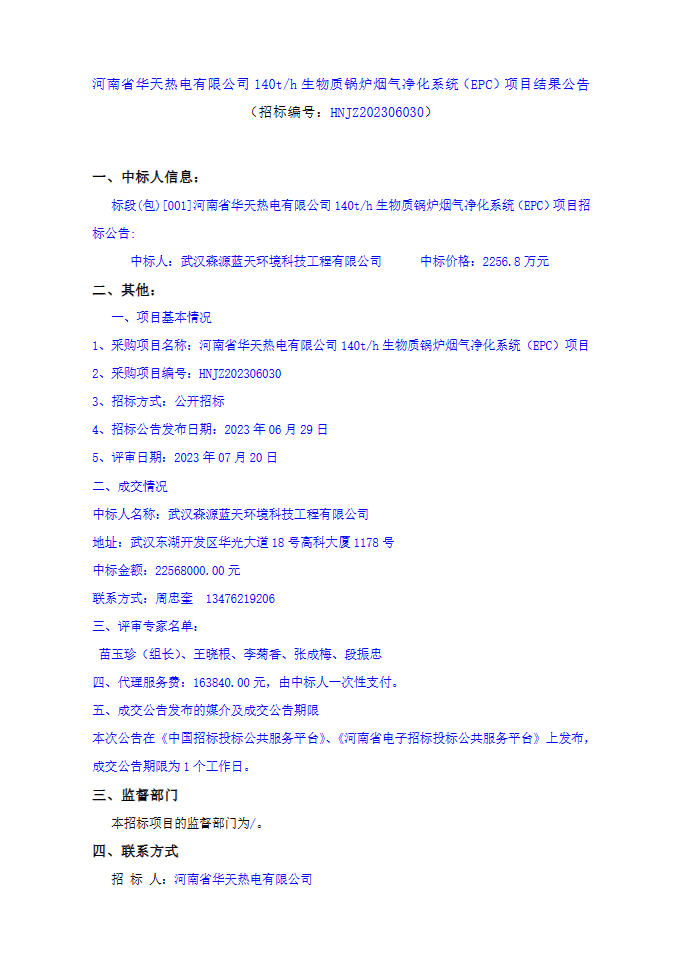法制日报提出政府应摸底“毒地”公之于众,新京报提出“毒地”信息公开别再靠倒逼了,由于用了这个“毒”字,就有了“一块土地之所以被称为毒地,就是因为它存在太多无人知晓的内幕,而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这样的评论。以至于有把雷洋之死与常外“毒地”的调查者和内幕知情者相联系,把这个“毒”字极富想象力的去理解,但谁能说清楚使用“毒”字的根据在哪里?如果把切尔诺贝利核泄漏区定为“毒地”,肯定有根有据,没有争议,但国内媒体所说的“毒地”,并非全部如此。

业内专家高胜达根据美国污染场地数量和中美两国制造业情况对比,对中国污染场地数量估计为30-50万块,这是不包括农业、矿山污染的工业企业污染场地数量估计,“毒地”之说提出后,很容易被公众认为这些污染场地都是“毒地”。毒,必然有害,属于污染且有危害类型,是否属实,必须先看场地污染类型、范围和强度,其次要根据污染场地拟作用途判断被污染对象可能遭受的损害风险,以便做出弃用或修复的决策。如果这两件事还没做,就不能一概而论的称为“毒地”。因为连毒源及其毒源危害评价标准都未确定,何来“毒地”之说。
常外事件是因为先有污染场地修复之举,后因常外学生出现症状被媒体据此事实冠以“毒地”的帽子,给常外学生淋巴结肿大等症状的毒源早早的下了结论,才使“毒地”声名大振。但是,调查到今天,哪位科学家能够把“毒地”之源与学生中毒症状找到输入响应关系,并给“毒地”定健康危害罪呢?这表明加个“毒”字,能将场地污染危害引向毒害公众健康,用公众健康来吸引眼球,但想做出科学裁判,就难为环境专家了。因为,常外事件的毒地造成空气、地下水质量恶化并影响学生健康的证据都需要跨学科的合作获取,不能简单根据环境污染数据下“毒地”危害健康的结论。这说明从污染危害到健康危害不能简单地跨越。

想从超标环境污染物的浓度得出公众健康受损的响应数据,则需要长时间累计,这是当今环境科学的难点,例如香烟可能导致肺癌患病率提高是一个多年数据验证的结论。又如,十几年前提出手机可能导致脑癌,现在证明这种推断得不到数据支持,但手机使用强度和频次与以前大不相同,这种推断又需要用新的数据找到支持。还有 PM2.5,中国和欧美因 PM2.5成分不同,中国肺癌、肺心病等病症的病因调查数据也会不同。这些都需要时间,都不是简单的下个“毒”字,引起关注就能解决的。
再回到场地修复,人不需要一棵树吊死,不需要一定优先在污染场地上开发,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使是“毒地”,惹不起还躲不起么?国外将可持续性修复定义为“实施修复技术带来的效果一定要大于修复工程的环境影响”,意指修复过程必产生不利环境影响,没有把握实现正面影响大于负面影响就不要轻易动手,所以环境规划院王金南教授提醒说,“没有足够的技术储备和经济能力,最好少翻开那些已经严重污染的场地,不能修复赚了钱,还二次污染了环境”。

至于土壤修复和前面所说的场地修复是两个不同的战场,不能等同。陈吉宁部长就治土市场提出“大治理不是几万亿,而是大过程”的观点,强调了风险管控的方向。人不吃土,吃的是土生土长的食物链,因此治土必须明确目的。从目标评估措施,不要为治而治。因为农田污染,可以更换土地作物避免食物链危害;可以通过提高有机质含量,从提高土壤质量入手減缓食物链危害;即使可能成为水污染源的工业重污染区,也应从除源、防淋溶、断径流等方面综合治理以控制污染危害,是个综合管控风险的过程。所以他强调治土是个大治理过程,重点强调风险管控,要管控土壤污染风险,通过改变土地利用方式,而不是简单依靠巨大的资金投入,对污染的土壤要加强监测监控,不让污染继续发展。这个定位,与世界各国多年形成的治土方略一致。
从治理投资应该让老百姓得到实惠考虑,不希望治土市场盲目投资,比如:为了让老百姓享受健康环境,应该把30-50万块“毒地”都治理好;为了让老百姓吃安全食品,应该把不能出安全食品的几千万亩污染土壤全治好,这样做名为源头治理,但这样干值得吗?代之以风险管控,不该用的污染场地不用,不可种食物链作物的土壤更换作物,需要跟踪监测积累数据的我们监测,需要通过示范工程验证技术、积累经验的,我们实干,这样做肯定人民欢迎,对治土大业更有好处。

期待媒体界慎重使用“毒地”,引导公众真正懂得风险管控的做法,先解决污染治理问题,确保环境质量达标,为最终解决污染影响健康命题奠定基础。原标题:“毒地”之词应慎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