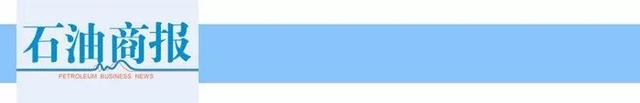
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多项指标领先世界。 在促进环境改善、应对气候变化、节约和高效利用资源的经济活动中,要弘扬战略思维,锚定新能源体系愿景,发挥绿色金融引领作用。 中海油能源经济研究院院长王震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就化石能源与新能源平衡发展提出了几点建议。

能源转型需要平衡好高质量发展、能源转型和能源安全的关系
石油商报记者:在世界能源转型不断推进的背景下,传统化石能源发展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但其“压舱石”地位尚未改变。 您对如何平衡传统能源与新能源发展有何看法或建议? 如何更好发挥绿色金融的引领作用?
王震: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和碳中和,立足我国能源资源禀赋,坚持先建立后发展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碳达峰行动,深入推进能源革命,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加快新能源体系规划建设,积极参与气候变化全球治理。
能源转型是一个渐进、长期的过程,其本质是协调好高质量发展、能源转型和能源安全的关系。 我国未来能源转型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2030年之前是碳排放达峰期,2031年至2050年是碳减排加速期。 其中,2031年至2035年可能是整体呈下降趋势但会出现略有重复的平台期,而2051年至2060年将是碳中和的决定性时期。
我们还要认识到,能源转型的最终目的始终是服务于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让每个人都能享受到优质和谐的生活。 过去10年,我国总体解决了能源“占有”问题,现在强调高质量发展,就是在“占有”的基础上实现“好”发展。
一是坚持战略思维,锚定新能源体系愿景。 在能源治理实践中,“面对经济困难,信心比黄金和货币更重要”。 有了共同的愿景,能源安全治理更容易实现系统韧性。 我们需要根据当前发展阶段不断完善和调整能源战略,使我们的锚定愿景越来越清晰。
二是坚持辩证思维,客观认识传统能源的作用。 形成能源安全韧性的大前提是能源系统不被巨大冲击“击垮”。 如果缺乏一定的底线,能量系统在遭遇冲击后就会彻底瘫痪,无法恢复。 基于我国资源禀赋特点,煤炭对我国能源安全具有基础性作用,不能简单、盲目地退煤。 预计到2060年,我国石油需求量仍将达到2亿吨,天然气将达到4100亿立方米。 天然气发电可以有效补充不稳定的可再生能源发电。
三是坚持创新思维,不断开拓绿色低碳领域。 美国页岩油气革命离不开其发达的金融市场、开放的矿权制度、技术创新和资源禀赋,但最重要的是企业家在不确定性中抓住机遇的创新创业精神。 构建能源安全和韧性,还需要坚持创新思维。 能源技术创新是能源大国竞争的主战场,也是确保能源产业链特别是绿色低碳产业链自主可控的关键举措。
四是坚持系统理念,不断提升能源治理能力。 深化能源体制改革,打破基于传统能源的能源治理体系,建立绿色低碳导向的能源产业发展模式,深入推进电力、油气等制度改革,不断提高绿色发展水平。能源低碳转型体制机制。 国际格局东升西落,可再生能源比重不断上升,能源科技快速发展,世界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实力潮起潮落。 这些新变化要求我们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全球能源治理体系改革。
能源转型不仅仅是脱碳,更要保证能源供应渠道的安全稳定。 同时,实现能源系统脱碳需要大量投资。 除了传统的投资方式和政府补贴外,还需要结构性金融工具来精准投资可再生能源、化石能源脱碳、基础设施建设等。 绿色金融对实体经济的调控延伸了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的概念。 企业绿色转型离不开ESG。 这是从三个维度评价企业运营的可持续性及其对社会的价值。 观念的影响。 但也需要强调的是,绿色金融的发展不能完全依靠行政手段,还必须依靠市场化手段,必须引入市场化机制。
绿色发展机制的核心是重构竞争优势
石油商报:绿色发展机制作为全球能源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您认为其核心是什么? 需要哪些能源经济学和政策研究?
王震:从历史上看,所有工业革命都伴随着能源革命。 从这个意义上讲,绿色发展机制的核心是在新一轮科技革命/技术革命竞争中获取优势的结合,即重构竞争优势。 碳中和愿景倒逼企业建立适合国际治理和经贸合作的机制,加快生产方式转变和业务结构优化。 在企业生产和采购链低碳化的指导下,产品和原材料的碳含量指标将成为与成本、质量、服务一样重要的竞争因素; 全球低碳金融的投资导向将使高碳排放行业和企业面临融资困难。 投资存在成本搁浅风险; 企业的生产行为受到各利益相关方的监督,企业的减排成本可以转化为企业的竞争优势。 将污染预防、碳减排和提高能源效率贯穿于生产过程,增强市场竞争力; 绿色消费将倒逼生产领域减排,推动工业、交通、建筑等领域节能低碳服务业快速发展。
对于“双碳”目标下的能源经济和政策研究工作,需要基于未来的可能性进行情景设计,大胆探索趋势,逐步模糊能源行业的边界。 首先,碳中和愿景将重塑企业竞争格局。 清洁低碳能源已成为更多企业减排、减少碳排放的必须。 传统能源企业与新能源企业的激烈竞争将导致行业边界更加模糊。 其次,传统能源行业的边界将变得更加模糊。 化石能源公司和电力公司可能会深度融合。 产业链不同环节将有更多参与者,或将出现多轮并购,产业结构调整将加速。 第三,能源品种的界限将变得更加模糊。 能源需求多元化将导致能源产品更多排列组合。 综合终端能源产品或将成为未来能源企业的重要选择。 此外,还必须加强技术跟踪研究。 我们对未来的想象更多是基于现有技术的前景,未来一定会有重大的技术突破。 如果没有技术革命,碳中和的愿景将很难实现。 这就要求研究人员具备国际视野、历史发展观、综合知识等,以及场景设计能力和模型思维能力。
国家石油公司能源转型须平衡好主体责任与新兴业务的关系
石油商报:未来,国家石油公司在继续稳步发展油气业务的同时,在基础设施、能源技术体系、新材料等方面还需要做出哪些调整?
王震:“双碳”目标加速能源产业从“资源主导、资本主导”向“技术主导、资本主导”转变。
基础设施方面,“大云物动智能链”与能源生产、能源运输、能源贸易等深度融合创新,系统灵活性和可靠性显着提升; 数字化、智能化产业规模化发展,能源设施无人化、自动化特征将更加凸显; 多元化、智能化的节能需求将推动未来原油管道、成品油管道、天然气管道、二氧化碳管道、氢气管道等五套智能管网的形成; 深化电力体制改革,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体系,适应清洁能源的不稳定性,建设具有“负荷随源或随源互动”能力的电网。
在能源创新方面,2021年至2030年,传统化石能源市场主体将加大对新能源产业的融入力度。 现阶段化石能源行业的技术创新将在节能技术、生产设施等方面进行,如余热利用、煤炭超低排放技术、热电联产技术等; 2031年至2050年,碳捕集与封存(CCS)技术将大规模发展。 在煤电主体作用逐步弱化的过程中,它将与气电联动发挥重要的调峰功能,储能需求将大幅增加。 2051年至2060年,化石能源主要属性将从燃料转变为原材料,碳基新材料技术体系已基本形成。
新材料方面,能源产业转型将加速新材料和循环经济发展。 随着可再生能源的大规模开发利用,相关稀有材料和关键矿产资源的需求将出现短缺; 未来能源地缘政治的重点可能从石油、天然气转向铜、锂、镍等金属,确保关键矿产资源供应链的安全稳定将是日益严峻的挑战; 新材料和循环经济成为支撑新能源产业规模化快速发展的重要基础。
国家石油公司在进行业务调整时,要依靠行业判断,尽可能匹配公司能力和业务优势,平衡主业和新兴业务的关系,发挥引领作用。 比如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和中国石化石油化工研究院,这两个科研院所不仅是企业的研究院,还肩负着培养研究生、博士等高素质人才的使命。 这表明国家希望科研院所能够承担专业领域的基础研究工作。 基础研究从根本上支撑技术创新,可能不会立即实现商业产品或价值,但没有持续基础研究的支撑,创新也是不可持续的。 同时,作为企业,要坚持市场导向,坚持价值理念,平衡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充分发挥科技创新主体作用,在制度和技术上取得根本性突破。机制,大力倡导原创性、引领性创新。 突破,发挥央企作用,实现科技自力更生、自力更生。
因此,在构建技术体系时,无论是需要广度还是深度,每个企业都需要根据自身能力来探索匹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