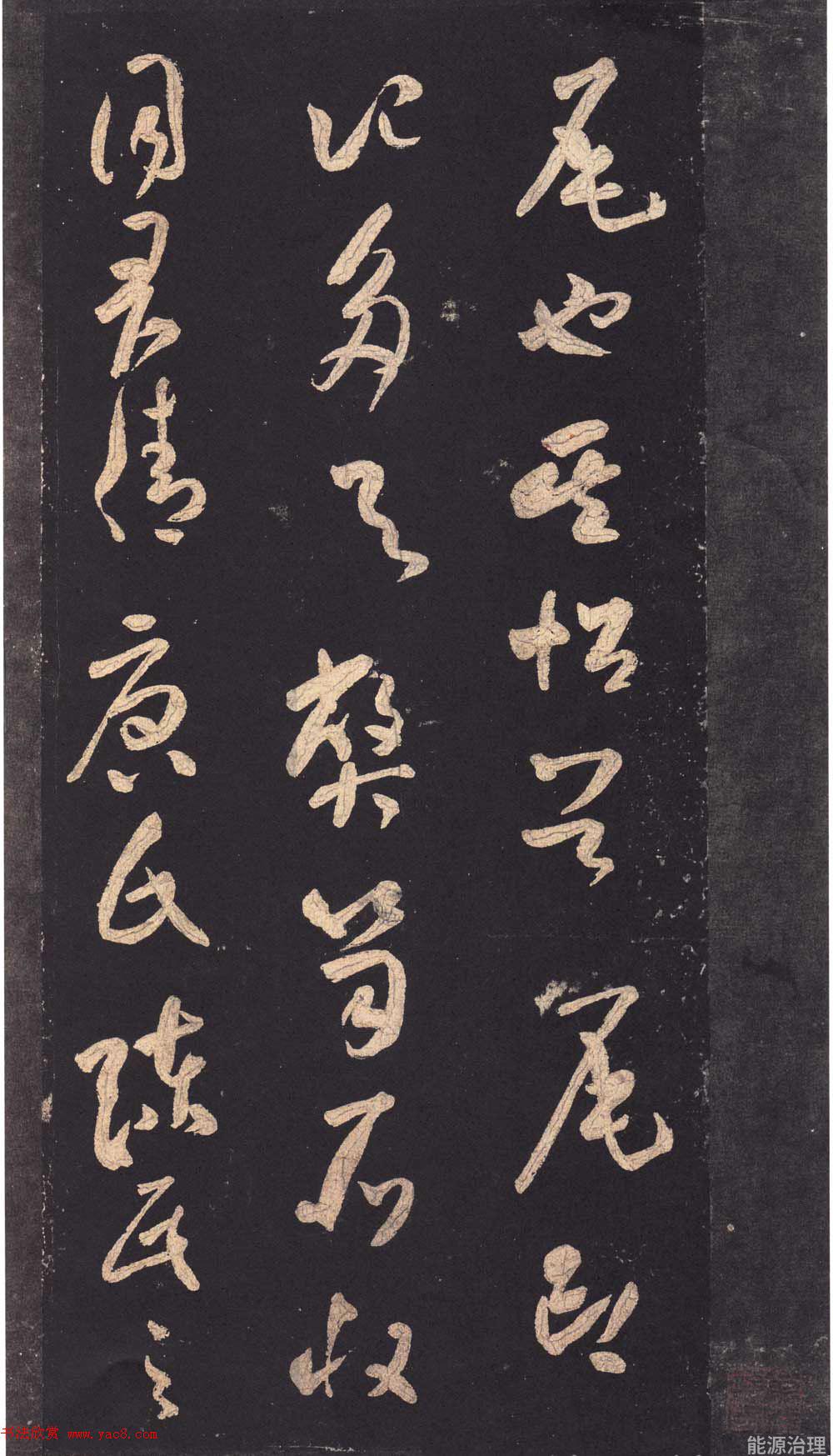近年来,全球能源治理日益成为全球治理领域的热点和焦点问题。 除了IEA、OPEC等传统国际能源机构外,ECT(全球能源宪章)、IEF(国际能源论坛)、IPCC等国际能源协调机制也积极发声,甚至二十国集团(G20)也积极发出自己的声音。 G20)是为了全球治理而成立的。 )现已成为全球能源对话的重要平台。 中方也在上述国际能源机构和能源协调机制中积极发挥作用,表明自己的看法和立场。
值得注意的是,页岩油气革命引发了全球能源格局的一些新变化。 这些新变化导致有关国家在国际能源问题上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发生变化,从而影响和推动以发达石油消费国(IEA)和石油生产国(OPEC)博弈为核心的全球能源治理的未来。种类。 为了通过参与全球能源治理更好地保护我国能源核心利益,我们认为在各种变化中,以下三个变化值得特别关注。
IEA转型为“全球能源机构”
当前,全球能源治理结构的基本格局是:以美欧为首的能源消费国利用IEA,通过推动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来施加影响和控制全球能源定价权。 同时,它们还积极利用G20/G8、WTO、ECT(全球能源宪章)、IEF(国际能源论坛)、IPCC等机制发出自己的声音,引领全球能源治理架构的方向。
其次,主要产油国通过OPEC实现维护产油国利益的政策诉求。 作为世界重要的油气生产国,俄罗斯自2009年起也试图通过天然气输出国组织(GECF)增加影响力。中国、印度等新兴能源需求国长期处于国际能源影响力之外。组织(它们既不是能源需求国组织的成员,也不是能源生产国组织的成员)。 为维护自身利益,主要采取与有关能源出口国进行双边谈判的方式,也通过各种能源协调机制表达自己的声音。
在各类国际能源机构和能源协调机制中,国际能源署(IEA)和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执行能力最强,影响力也最大。 由于这两个机构的成员拥有相同的价值目标,成员国愿意采取一致行动,实现共同的价值目标。 这是IEA和OPEC发挥作用和影响力的关键和前提。
其他机构或机制,如G20/G8、ECT、IEF等,缺乏这两个关键先决条件。 它们的权威性和代表性高于IEA和OPEC,但行动能力和影响力却远远落后。 由欧盟发起并主导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虽然表面上得到了几乎所有国家的支持,影响力很大,但由于排放分担的巨大差异,一直被拖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减排责任。 达成可行的协议和计划一直很困难。
面对成员国能源供需格局的变化和各国对气候变化日益关注,IEA作为发达能源消费国组织,不断努力扩大成员国范围和职能,谋求在未来全球能源治理结构中继续占据主导地位。 甚至成为真正的“全球能源机构”。 为此,IEA早就表示欢迎中国、印度等新兴能源消费国和俄罗斯等能源生产国加入IEA。 另一方面,它也一直试图在气候变化等能源和环境问题上发挥更大作用。
例如,早在2011年,IEA官员就表示,IEA最适合承担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减排的MVR(可测量、可报告和可验证)工作,因为只有IEA有能力测量所有排放量。 全国能源电力数据统计分析。
但需要看到的是,即使未来IEA修改会员门槛条件、扩大代表性,随着价值目标不完全一致的成员加入,IEA的一致行动能力也将不可避免地下降。 而且,适用于现有成员国的协调行动机制,例如危机时共享石油的紧急机制,并不适用于所有新成员国。 因为“自动共享”的前提是高度的信任,而俄罗斯和中国在这方面显然还没有与现有的IEA成员国建立足够的信任。
能源安全被气候变化担忧取代
自1960年主要产油国成立OPEC和1974年OECD国家成立IEA以来,全球能源治理基本围绕发达石油消费国与石油生产国之间的博弈展开。 从1974年IEA成立到20世纪末,OECD国家占全球石油消费的比重一直保持在60%以上,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石油消费群体。 OPCE成员国的全球石油产量份额除20世纪80年代长达8年的两伊战争和1990年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外,基本保持在40%以上,是全球最重要的石油生产集团。 。
作为供需双方,这两大群体时不时地互相争斗,但他们密不可分,并且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能源安全。 对石油消费国来说是“进口安全”,对生产国来说是“出口安全”。 石油生产和供应中断将对供需双方产生严重不利后果。 因此,“能源安全”自然成为全球能源治理的主流价值目标。
但进入21世纪以来,1995年启动的国际气候谈判影响力日益增强。 目前,联合国90%的成员国和3000多个国际组织参与了国际气候谈判。 尽管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大国与小国立场存在巨大差异,《京都议定书》以来的多次谈判都没有达成任何操作性协议,但这并不妨碍气候变化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 全球能源治理最重要的焦点。
我们知道,欧盟是国际气候谈判的最初发起者和全球减排的主要推动者。 欧盟这样做并不是因为“道德高尚”,而是因为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其能源需求增长放缓甚至下降,这大大减轻了其对能源安全的焦虑。
英国石油公司数据显示,1996年至2012年欧盟天然气消费量年均增长率仅为0.5%。 2006年,石油消费再次进入绝对下降阶段,2006年至2012年平均下降2.7%。
在这种情况下,欧盟以气候变化(环境问题)作为参与全球能源治理的价值主张,可以达到“一石二鸟”的效果:一方面欧盟获得道义优势参与全球能源治理结构,从而主导全球能源。 治理结构的未来走向; 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各国选民同意增加对可再生能源的补贴,提高可再生能源的比例,减少化石能源的比例,最终增强欧盟的能源安全。
从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能源治理的趋势来看,欧盟的战略是成功的。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虽然欧盟因内部经济问题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力度有所放缓,但方向没有改变。
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美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消极立场有所改变,但在履行减排承诺方面进展甚微。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政府最近开始对化石燃料发电厂的二氧化碳排放标准制定更为激进的政策。 2013年9月20日,美国环保局公布了未来新建发电厂碳排放标准的最新提案。 新标准要求美国新建的燃煤发电厂每兆瓦时发电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不得超过 1,100 磅。 根据该提案,如果新的燃煤电厂没有配备碳捕获和储存(CCS),将被禁止建设。
但这一政策本质上带有一定的“作秀”成分。 因为美国页岩气革命后,天然气价格低廉使得天然气发电迅速取代煤炭发电。 限制煤电在减排方面占据“道德制高点”,同时对国内产业并无实质影响。
美国立场变化的背景也来自于美国能源供需格局的重大变化。 一方面,页岩油气革命使2008年以来美国油气产量增长出现明显拐点:2008年至2013年,美国石油和天然气产量五年分别增长47.6%和20.5%。年均增长率分别为8.1%和20.5%。 3.8%。 另一方面,美国石油消费自2005年达到半个世纪以来的新高后,开始呈现明显下降趋势。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加速了这一趋势。
2008年至2013年五年间,美国石油消费绝对量年下降5.1%,年均下降1%。 石油消费和生产的潮起潮落导致同期美国石油净进口量大幅减少,五年内年净进口量下降了33%。 预计到2016年,按北美安全可用石油净进口量计算,美国进口依存度将下降至20%左右。 如果考虑到天然气部分替代石油(如发电、LNG汽车等),对国外石油的依赖度可能会进一步降低。
美国能源安全形势的实质性改善,为美国的全球战略和参与全球能源治理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与欧盟争夺气候变化领导权、夺回道德制高点已成为合理选择。 因此,在全球能源治理架构两大主导力量——美国和欧盟的共同推动下,气候变化已逐渐取代能源安全,成为未来全球能源治理的主流价值目标。
可能损害世贸组织自由贸易原则
未来欧美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能源治理价值观从能源安全转向气候变化,很可能危及现行世贸组织自由贸易原则,从而严重影响中国的贸易利益。
从欧盟和美国在多轮气候变化谈判中的表现可以明显看出,他们非常希望中国为全球减排做出“巨大贡献”,但却没有考虑到其承载的后果。中国经济发展的能力根本就没有。 为了最终达到目的,欧美甚至不惜破坏世贸组织的自由贸易原则。 这一点在2009年12月哥本哈根谈判之前就已经显现出来。
2009年6月,美国众议院以微弱优势通过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气候法案”——《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 该法案授权美国总统采取“边境调整”措施,对一些发展迅速但在2020年起减少本国温室气体排放方面做得不够的国家征收惩罚性“碳关税”。年底,由于存在巨大分歧,欧盟和美国表示打算采取单边贸易措施限制发展中国家产品的进口。
2011年12月,欧盟最高法院规定从2012年起对外国航空公司征收碳排放关税。所有外国航空公司的配额为2010年碳排放量的85%,超出部分将征收碳排放关税。 由于美国、中国、俄罗斯等欧盟以外主要大国的反对,欧洲议会环境委员会投票决定暂停对外国航空公司征收碳税。
不过,据媒体报道,欧盟近日再次决定从2014年3月起对外国航空公司征收航空碳税。
短期内,美国不会对其进口产品征收“碳关税”,因为在当前的中美贸易格局下,征收碳关税会损害双方利益。 而且,美国法律还规定“这项规定要到2020年才会启动”。 但随着美国主导的TPP自贸谈判的推进,以及中国替代产品在东南亚等国的崛起,对美国来说,有必要动用“对中国征收碳关税”的大棒。国际谈判中的“进口”。 中国施压的效果将越来越明显,对中国产品征收碳关税“利大于弊”的时刻一定会到来。
我国作为世界新兴能源需求大国,在全球能源治理结构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几乎所有国际能源机构和各类协调机制都积极邀请参与或与中国保持密切联系。 看来,没有中国的参与,任何国际能源机构和协调机制的“全球性”都会大打折扣。 但在这“热闹”的景象下,我们需要保持清醒的认识。
首先,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全球能源治理的未来趋势对于中国等新兴发展中国家来说总体上是“弊大于利”。
二是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作为能源需求不断上升的发展中大国,其核心利益与美国和欧盟主导的全球能源治理主流价值观存在差异。
现阶段,能源安全仍然是我国参与全球能源治理的核心价值目标。 这就决定了,虽然需要积极与现有国际能源机构沟通合作,参与各类国际能源对话,但单纯加入欧美主导的国际能源机构或协调机制,并不能自动实现我国在能源领域的发展。场地。 “核心利益诉求”。 我国应对这一情况有清醒的认识、长远的规划和应对措施。